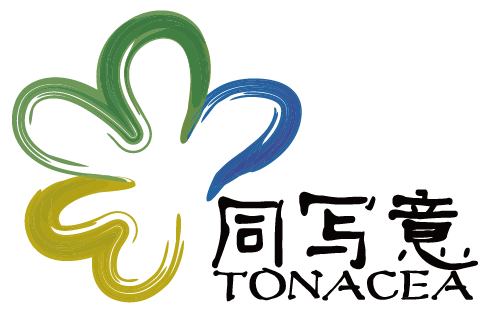当制药巨头,纷纷撤换CEO
更新时间:
2026-02-13 18:52
阅读量:

2月12日,在巴黎,赛诺菲董事会做出了一个与六年前相反的决定。
他们没有像2019年那样,欢迎Paul Hudson领导这家制药巨头,而是将其CEO的聘期定格于2月17日。消息传出后,赛诺菲股价盘前暴跌6%,投资者用脚投票。
早前两天的2月10日,南半球墨尔本,CSL董事长Brian McNamee也宣布,CEO Paul McKenzie因不具备公司所需的技能而“退休”。此时,距离备受关注的CSL半年业绩报告披露还有不到24小时,市场措手不及。
净利润暴跌81%,叠加人事巨变,令这家全球最大的血浆企业的市值加速下滑。其股价在18个月内几乎腰斩。
这些动作,形成了某种理解生物制药发展现状的互文语境。
两家公司都曾经辉煌过,都在核心产品面临专利悬崖或需求疲软时押注研发转型,又都在2025年遭遇关键临床失败或政策寒流。更微妙的是,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启用了“老人”:赛诺菲请回曾经效力15年的老将Belen Garijo,CSL则让33年司龄的Gordon Naylor临时掌舵。
这并非孤例。近年来,诺和诺德、GSK等跨国药企都选择撤换CEO。如果算上区域负责人,这场换帅潮的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。密集程度,实属罕见。
当“重磅炸弹”步入暮年,当研发投入不再线性兑换成股价回报,董事会正在重估一个核心问题:什么样的CEO,才配得上下一个十年?
TONACEA
研发困局
Hudson离开之际,赛诺菲并非没有成绩。
这家曾被诟病“法式保守”的公司,被Hudson从糖尿病和心血管领域拖出来,押注免疫学和肿瘤学。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,Dupixent一度做成年销售额141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畅销药。此外,他还主导剥离消费者健康业务Opella的控制权,让赛诺菲彻底转型为纯处方药公司。
Bloomberg Intelligence分析师承认,Hudson显著改变了赛诺菲文化,提升了其全球站位,并规划出公司到2030年的盈利增长路径。
但资本市场不买账。
Hudson六年任期,赛诺菲股价仅微涨1%,而阿斯利康同期翻倍,诺华也几近翻番。2025年,赛诺菲股价累计下跌23%。投资者质疑,Dupixent的核心专利2031年到期,而接替它的“重磅炸弹”迟迟没有出现。
2023年,Hudson推出激进的“加速新药上市”计划,研发预算在两年内激增20%。可2025年,三项后期临床以“混杂甚至负面”的结果收场。
其中,实验性多发性硬化症药物tolebrutinib在关键III期失败,FDA以肝损伤风险为由拒绝另一适应症上市;曾被寄予厚望、被视为Dupixent“天然继任者”的特应性皮炎候选药amlitelimab,临床数据好坏参半。
1月底的业绩会上,Hudson罕见地流露疲惫:“如果2020年你问我,赛诺菲需要五到七年吗?我当时斩钉截铁说不会。我们更聪明、更强,一定能更快——可惜事与愿违。”
赛诺菲董事会显然不打算再等。
继任者Garijo,65岁,西班牙人,曾在赛诺菲任职15年,主导过Genzyme收购后的整合。过去五年,她担任德国默克集团CEO,这家业务横跨制药与半导体的工业巨头在其任内股价下跌14%——甚至比Hudson掌舵的赛诺菲还糟。

市场第一反应是困惑。投资者质疑,一个在自己任内未能推动制药部门增长、研发履历并不显赫的CEO,凭什么解决赛诺菲最棘手的研发效率问题?
但Jefferies分析师提出了另一种叙事框架。在默克集团,制药部门从来不是优先级——家族控制下的所有权结构和战略重心长期偏向生命科学工具业务。“如果非要说的话,能在制药业务上阻止进一步下滑,本身已相当令人印象深刻。”
赛诺菲董事长Frederic Oudea的表态,则透露出更深层的考量。他称赞Garijo“对本公司文化了如指掌”。言外之意:Hudson始终没有完全驯服这家法国公司。
英国籍的Hudson与法国建制派的关系一直微妙。
2020年COVID初期,在采访中,他暗示“美国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获得赛诺菲疫苗”,触怒爱丽舍宫。
而2024年,Hudson主导将消费者健康部门Opella控股权出售给美国私募基金,法国政府紧急干预,最终以保留董事会席位和就业承诺收场。同年4月,他与诺华CEO Vas Narasimhan联名在《金融时报》发文,抨击欧洲药价封顶机制——在医疗体系由国家买单的法国,这种立场并不讨喜。
今年1月,赛诺菲退出法国制药行业协会Leem,Hudson本人则准备在2月出任美国游说组织PhRMA主席。
一位熟悉赛诺菲董事会的人士私下评论:“Hudson做了所有正确的事,除了学会如何在这里生存。”Garijo则不同。当媒体问及是否会说法语,她回复了一个单词:“Oui。”
Jefferies分析师认为,赛诺菲的管理层调整可能尚未结束。Garijo的真正挑战不是文化融入,而是如何在两三年内拿出实实在在的研发管线成果。
赛诺菲将在4月29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,届时,将正式表决Garijo的董事任命。公司同时提请修改章程,将CEO年龄上限从65岁上调——一项显然是量身定做的调整。
65岁的Garijo成为赛诺菲首位女性CEO。但她要面对的不是庆典,而是一个市值折让、管线青黄不接、投资者耐心告罄的困局。
TONACEA
扩张的反噬
如果说,赛诺菲的故事围绕研发挫折展开,那么CSL的情节版本则复杂得多。
McKenzie的“退休”来得突然,市场不断猜测,这位CEO是“主动离开还是被赶走”。随后的业绩会上,身为CSL董事长的McNamee直言不讳:“他不具备我们未来需要的技能。”
这家血液制品巨无霸,曾经是澳大利亚资本市场的神话。从墨尔本一家政府血清实验室起步,CSL花了三十多年,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多次收购而不断扩张,成长为澳大利亚除矿业领域外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公司。
McNamee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CEO期间,将CSL打造成全球血浆分馏领域的龙头之一,市值一度突破1400亿澳元。
但时过境迁。过去18个月,CSL股价近乎腰斩。

半年报披露的数字加剧了恐慌:报告期内,净利润暴跌81%至4.01亿美元,商誉减值高达11亿美元,主要涉及Vifor和Seqirus两个业务板块。核心血浆业务CSL Behring收入下降7%,拖累整体营收下滑4%。
种种问题都非一日之寒。
最大的包袱,来自2022年那笔近120亿美元的收购——CSL以史上最高代价拿下瑞士肾病药企Vifor Pharma。当时,市场普遍看好其进入铁缺乏和肾科领域的战略协同,但整合效果远不及预期。
Platypus Asset Management投资主管Prasad Patkar表示,这笔交易“绝对是一笔烂摊子”,只不过,CSL核心业务的持续良好表现掩盖了问题。
2015年,CSL以2.75亿美元从诺华收购Seqirus,这极大地促进了其疫苗业务的发展,以至于扭转颓势。而这场“翻身仗”的主导者,便是此次临危受命接任McKenzie的Naylor。
可惜,Seqirus的好景也不长。2024年,CSL酝酿将其分拆独立,却在10月突然叫停——原因是美国流感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,直接动摇了估值基础。自2025年Robert F. Kennedy Jr.出任HHS部长后,美国疫苗接种意愿持续走低。
CSL的血浆业务,则面临两大逆风:中国对白蛋白的新规压低了需求,而基因疗法正在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侵蚀血友病等传统市场。
晨星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,CSL的核心问题并非竞争力丧失——它在免疫球蛋白市场仍有份额增长,毛利率环比改善,且与武田、Grifols形成稳定的寡头格局——而是管理层在预期管理上的连续失误。
这种讲法得到了投资管理公司Ten Cap创始人Jun Bei Liu的认同。
在其看来,尽管管理层不断保证,但过去一年来,CSL的财务业绩持续恶化,投资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。就连McKenzie离职的公告时机也“混乱”:收市前几秒钟发出,投资者来不及反应,次日股价直接低开5%。
作为代理CEO,Naylor现年68岁,是在CSL服役33年的元老。2000年代,他曾担任公司CFO,后来执掌Seqirus并完成扭亏为盈。McNamee将代理CEO的任期设定为一年,同时启动全球范围内的CEO遴选工作。
CSL维持了全年增长2%至3%的营收指引,并将股票回购额度扩大至7.5亿美元。问题是,市场需要的不再是回购,而是证据。
试想一下,如果一向以业务可预期著称的公司连CEO火速被裁都预测不了,投资者又怎么会轻信一两句口号?例如,失望至极的Patkar就透露,他主管的基金在2025卖掉了所有CSL的股份。
TONACEA
换帅潮
赛诺菲、CSL相隔万里的两场换帅,被2月的时间线并置在一起。而倘若把镜头拉远,公众还会发现,这只是过去一年全球制药业人事版图剧烈重构的两个切面。
2025年第一季度,诺和诺德旗下司美格鲁肽大卖,超越默沙东的Keytruda,登顶“药王”。然而就在5月,该公司CEO Lars Fruergaard Jørgensen宣布离任。
外界猜测,让这位供职34年的元老从CEO一职退下,主要是因为诺和诺德的股价自去年高点已跌超50%,市值蒸发一度超4000亿美元,而下一代药物临床试验结果不及预期,在美国减肥药市场又节节败退。
随后的8月,一位从公司内部成长起来,但却并非丹麦人的Maziar Mike Doustdar,开始执掌这家深陷增长困境的巨头。
9月,GSK也宣布,掌舵九年的CEO Emma Walmsley即将卸任,由CBO Luke Miels自2026年1月正式接棒。
Walmsley的离任比合同到期更早。尽管她在过去几年完成了GSK消费健康业务Haleon的分拆,摆平了Zantac相关诉讼,将公司重新聚焦为纯粹的生物制药企业,资本市场却并未买账:九年间,GSK股价累计下跌约11%。
投资者无法忽视的事实是,当同行在COVID疫苗和肿瘤免疫领域接连突围时,GSK的管线始终缺乏重量级接力资产。
同样在9月确认的,还有默克集团的CEO新人选——由公司电子业务CEO Kai Beckmann升任。
排资论辈,Beckmann更是一员“老将”。他自1989年加入了默克集团,担任信息技术系统顾问,四年半后,晋升为公司系统与数据中心管理主管,其后历任IT基础设施负责人、信息管理与咨询负责人、CIO等职务。
2017年是Beckmann的一个重要转折。他就任默克集团高性能材料业务CEO,主导该业务全面转型为电子科技业务,成为和生命科学、医疗健康并列的默克三大业务之一。自2021年起,Beckmann担任默克集团电子科技业务CEO。
过去几十年,大型药企CEO的标准画像,往往是“增长执行者”:擅长管线组合管理、并购整合、股东回报。
无论是赛诺菲Hudson,还是CSL的McKenzie,都属于这个世代。他们在任内完成资产剥离和战略聚焦,却也都在“研发产出”这个无法外包的硬核问题上丢分。

与之对比,作为继任者的Garijo与Naylor,则属于另一类CEO的回归:深谙组织基因的“文化修复者”。董事会认为,赛诺菲需要的是一个能与政府等各界打交道的角色,CSL想找的是能重建投资者信任、厘清战略优先级的舵手。
2026年,一场新的制药行业转型愈演愈烈。
COVID带来的现金流和红利已消耗殆尽,剩下来的问题,是那些原本就存在的、只是曾被掩盖的:专利悬崖如何跨越,研发效率如何提升,明星产品之后公司往哪里走……
不同公司给出不同答案。有的选择请回熟手,有的选择跨区域调兵。不过底层的共识是,CEO的任期正在变短,董事会的耐心正在变薄。
赛诺菲没有给Hudson第七年。CSL没有让McKenzie完成转型。诺和诺德、GSK、默克集团等巨头,也迫切告别它们的“旧爱”,寻找下一个能带来增长点的“新欢”。
对于仍坐在CEO这个位置上的人来说,信号足够清晰:当奇迹迟到,董事会不再等待。
上一页
下一页
相关新闻